曾经沧海难为水庄棫的沉浮史
庄棫(1830——1878),字中白,一字利叔,清代词人、学者,号东庄,又号蒿庵。丹徒人,生于道光十年(1830)。光绪四年(1878)卒。享年四十九岁。著有《蒿庵遗稿》,词甲、乙稿及补遗附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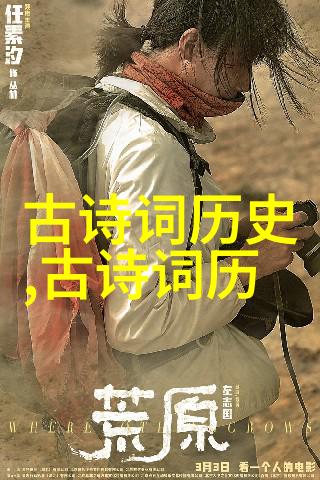
庄棫论词比谭献更重视“比兴”。他为谭献的《复堂词》作序,其中就特别说到:“家国身世之感,未能或释,盖风人之旨也。”——清·庄棫《复堂词序》关心国家,关心自己身世的这种感受,无法解脱。这时风人,即指从《国风》里的“风人”,这个宗旨。但是,他说呢,“世之狂呼叫嚣者,且不能知仲修之诗,乌能知仲修之词哉?礼义不愆,何恤乎人言。”——清·庄棫《复堂词序》且不能知谭献之诗,因为他是谭献字仲修。他又说,
夫义可相附,而义即不深;喻可专指,而喻即不广。托志帷房,以眷怀君国。

喻,比喻,“喻”可以专指,但其意并不广泛。他说虽然一直从宋以来,有很多人的作品,但是能够合乎这个比兴之旨的“合者鲜矣。”为什么呢?有的是“又或用意太深,其辞为义掩。虽多比兴之旨,不发缥缈之音。”——清·庄棫《复堂词序》或者是,有些人不能够真正在词里面寄托那种托志帷房、眷怀君国的那种深意。或者呢,用意太深,其结果被那个词表面掩住了。而虽然里头有比兴的这个宗旨,但是没有那种缥缈的、寄托的情感表现出来。
所以他就说,“自古至今,无一而非此道耳。”这是因为他一方面要强调这个,要托志帷房,以眷怀君国。一方面,又要强调有比兴。如果你只是有眷怀君国这一个意思,但是你只是一味地狂呼叫嚣,以为慷慨,那是不对。如果你纠正了这个,就变成了平庸,所以他说真正能够像那个古代文人的涵义太少,可以看出和谭献相比,他论诗更偏向于崇尚柔厚,并对待那些雕琢曼辞、“靡曼荧眩”的弊病持批判态度。而在他的观点中,对于抒情手法,更倾向于追求那一种以浅显入微,使每一次抒情都蕴含着丰富内涵和层次分明的情感表现,这种方式对于后来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尽管如此,在他的作品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许多精彩绝伦的情景描写,比如他的[唐多令]一首:
灯焰似凝脂,

红心草恐非。
幂烟煤一样迷离。

照得空庭都四彻,
原不藉,
蜡成堆。
这盏灯火,小小一盏灯火,看起来简直不像一根灯芯照出来的,它一堆烟煤那样迷离地照得空庭,都四面都照到了,都堆砌着蜡成堆。但是下面的一转,却写出了影隔便难知,只留给众多窥探者的光芒,也曾让镜里蛾眉见证过这一刻。这盏灯也曾照过镜里边美女的人生境遇,这样就在空庭中既展现了一种自我安慰与自负,同时也透露出一种因缺乏了解而感到困扰的心情,以及最后在窗外北风结冰时显得那么微弱,那么凄凉,这一切都是通过那盏微弱而又充满力量的小小灯火来体现出的,从而展示了作者自己的处境和内心世界。在这样的情境下,可以看出这种使用隐晦但却充满层次性和丰富性的语言艺术手法,是如何将抽象的情感具体化,将个人内心世界投射到外部环境中的过程,让读者通过细腻的情景再现去领略作者内心世界的一片片画卷。此外,还有一些如同《相见欢》的作品,如:
深林几处啼鹃,
梦如烟。
直到梦难寻处倍缠绵。
蝶自舞,
莺自歌,
总凄然。
明月空庭如水似华年。
这些抒发旧梦难寻、华年逝水的人生感慨,也颇具动听,但同时它已经逐渐落入常规模式后期文学界一些评论家认为陈廷焯评价此句作为超越古今则显得有些过誉了。不过,在整体上来说,不管是在哪个方面,或许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探讨并评估这些评价所带来的影响力以及它们如何塑造我们对某个时代文学家的认识。在考虑历史背景与文化氛围时,我们应当注意到当时社会上的各种压力与限制,以及他们怎样影响着当代人物选择其艺术道路以及最终完成其作品的事实情况。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应该更加审慎地分析并评估这些评价,并努力理解它们背后的故事及其意义,从而更好地了解那个时代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学发展的一个角度。这也是为什么现代研究人员会不断推翻过去人们关于某位大师或特定流派所持有的观念,并尝试重新构建一个更加全面且客观的事实基础,这样的反思对于我们的理解非常必要,因为它帮助我们去除那些基于假设或偏见形成的地球磁场,使我们的知识体系更加完整无缺。